主播與MCN機構合同糾紛頻發:直播兩個月賺2000元,解約卻要賠5萬元?
在一些網絡主播與MCN機構的合同糾紛中,收益分成比例與違約金數額成為爭議核心——直播兩個月賺2000元,解約卻要賠5萬元?
閱讀提示
“有效直播時長”如何算?主播收入“拿多拿少”怎么定?違約到底賠多少?近年來,伴隨直播行業的飛速發展,網絡主播與MCN機構之間的合同糾紛頻發。
每天直播數小時,兩個月收入僅2000元?簽訂合作協議后,因收益遠低于預期,主播小徐選擇停播,被所在公司索賠5萬元違約金。
近日,吉林市船營區人民法院披露了該案的判決結果。考慮到小徐合同履行僅兩個月、收益不理想,且其作為行業新人法律意識不足、過錯有限以及所在公司證據不足等情況,法院酌情將違約金調至1000元。
在剛剛過去的“雙十一”,直播帶貨創新消費場景。伴隨直播行業的飛速發展,網絡主播與MCN機構之間的合同糾紛頻發,其中,收益分成比例與違約金數額是部分案件的爭議核心。
部分收益分成條款約定不明
記者注意到,在一些網絡主播與MCN機構簽訂的合同中,存在設置高強度直播時長、工作標準不明、違約條款模糊等情況。
從事電商直播領域相關工作數年的徐澤偉向《工人日報》記者提供了一份《主播合作協議》,稱該協議由某MCN機構制作并要求合作主播簽訂,“很多MCN機構使用這類合同模板”。
記者在這份合同中看到,雙方約定,“主播每月直播時長不低于26天,每天直播時長不低于6小時,每月直播總時長不低于156小時”。若主播有當月直播時長低于協議約定等“違約情形”,“甲方有權暫停補發保底收益、扣減或停發直播分成、直播帶貨收益或短視頻收益、停止資金扶持,并追回乙方已自提收益、補發的保底收益和短視頻收益以及甲方的前期實際投入費用”。
但是,“如何計算直播時長”是一些主播較為困惑的地方。在上述《主播合作協議》中,記者發現,關于“直播時長要求”的條款中寫明,“符合甲方直播內容要求的直播時長,方可確認為有效直播時長”,而合同中關于“直播內容”的要求則相對模糊,缺乏具體細則。
關于雙方的收益分成,該《主播合作協議》及其附件《主播績效方案》中寫明,主播第一個月的保底收益為2000元,達成特定條件可獲得分成。MCN機構將依據凈流水與合作收益向部分主播提供1%~14%的分成,且MCN機構有權根據政策、市場、效果等更改分成比例。
在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范圍看來,雖然部分主播與MCN機構之間屬于平等主體的經紀合同關系,但有的MCN機構利用優勢地位、渲染行業耀眼光環進而吸引勞動者進入這一行業,實際簽訂的是顯失公平的經紀合同。
當出現合同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情形時,該如何處理?在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審結的一起案件中,主播小劉與經紀公司因利潤分成產生糾紛,法院判定雙方以協議約定的中位值進行分成。該案審理法官表示,對于此類情形,應首先由雙方當事人進行協商,如果仍不能確定,則應以鼓勵交易、實現公平為目的,促使合法成立的合同繼續履行。
違約金過高可能面臨調整
記者在上述《主播合作協議》看到,“違約責任”部分條款寫明,主播每日流水需返回公司賬戶內,如果當天未返,需承擔10倍賠償。若主播在任何第三方平臺發布侵害公司名譽的文章、視頻或發布雙方達成的協議、溝通事宜等行為的,應支付公司50萬元違約金。
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趙虎表示,違約金是否被法院支持一般受兩方面影響,即合同是否有明確約定以及約定金額是否過高。判定違約金是否過高通常以MCN機構的實際損失等為基準,若違約金遠超其實際損失,法院可能酌情下調。
記者了解到,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第34批指導性案例明確,網絡主播主張合同約定的違約金額明顯畸高請求人民法院予以調整的,在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主播從平臺中已經獲取的實際收益為參考標準,結合網絡直播行業的特點,充分考慮平臺的前期投入、平臺流量、主播商業價值等因素進行合理判定。
除了民事合同,一些主播與MCN機構構成勞動合同關系,也面臨著收益分成與違約金相關爭議。
曾在北京某在線教育機構擔任全職主播的呂茹告訴記者,一些產品或服務的品牌方會開設內部直播間并招聘主播、運營崗員工,按照傳統勞動合同中的員工管理主播。“有些公司做在線教育,會聘請主播在公司的直播間售賣虛擬課程包或實體教材,要求主播每天打卡上班,并根據成交額計算主播和運營崗位績效。”
在北京中首律師事務所主任胡勝國看來,當前主播與MCN機構的法律關系呈現多元化特征,既有呈現“支配性勞動管理”特征的勞動關系,也有通過民商事合同達成的合作關系,“雙方法律關系對合同的有效性及后續維權流程影響較大”。
明確法律關系性質與合同條款
“不同的法律關系性質意味著法律適用的差異。”范圍分析認為,若認定主播與MCN機構之間存在勞動關系,則合同中關于直播時長、績效核算、打賞分成、違約金等的條款都應遵守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相關規定。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法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沈建峰告訴《工人日報》記者,“無論主播與MCN機構之間構成勞動關系還是合作關系,合同條款中都應明確雙方收益分成的計算標準、支付節點,且違約金設定需和實際收益損失掛鉤”。
沈建峰認為,在立法層面需進一步回應數字時代靈活就業特征,在勞動保障與契約自由間尋求平衡,分類施策,解決“既受管理又有一定自由”的用工模式法律適配問題。“行業組織可以推出分類合同范本,明確工作內容、收益分成、違約金設定等必備條款,規范約定不明情形的補充規則,從源頭減少分歧。”他建議,對于培訓期主播應著重關注其勞動權益保障問題,對頭部主播則著重約定競業限制合理范圍。
趙虎提醒主播從業者,若需與MCN機構簽訂勞動合同,應警惕“帶貨額不達標扣績效”等可能將MCN機構經營風險轉嫁給主播的條款。
“如果簽訂民事合同,則需重點關注權利義務平衡性,比如獨家合作條款是否匹配資源支持、明確收益計算方式,避免歧義條款或隱性扣減條款,并核查違約金合理性。”趙虎說。(徐澤偉、呂茹為化名)
本報記者 陳丹丹
《工人日報》(2025年11月20日 06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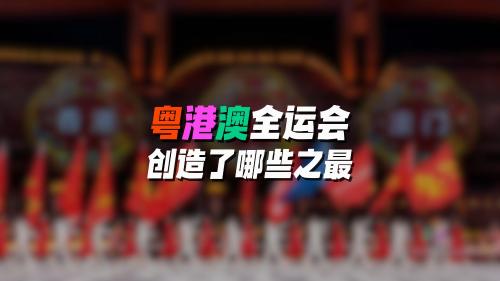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